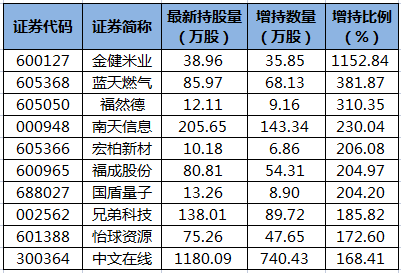引言
南北朝隋唐时期,粟特金银器,改变了中原人的审美方式和生活方式——尤其在开放繁荣的唐代,西方文化因素融进中国人制造的金银器中,具有粟特文化因素的金银器受到人们的喜爱。
目前胡瓶与壶、银带把杯、银碗、银盘、银碟等在丝绸之路河南道青海一带鲜有发现,但根据都兰墓葬已出土的金牌饰、银戒指、管状器、球(珠)饰、金银带饰和金银饰片等金银器,也可以窥探出其中较为典型的粟特文化因素。下文从都兰出土金银器的铸造工艺和图案纹饰两个大方面进行论述。
整片金属制造
河南道青海都兰出土的金银器中,各式联珠纹、卷草纹金牌饰,鹿形饰片,各式忍冬纹银饰片及包在木片上的忍冬镀金银条,均是由整片金属锻造而成,“普遍使用捶操技法作为金属成型的主要手段。

器物表面为全部或局部镀金,绝大部分器物以镂空形式表现纹饰的浮雕效果”,这些特点与同时期的唐代金银器铸造方式有所区别。
捶揲和阴刻
捶揲和阴线浅刻铸造技法在都兰出土金银器中也较为常见,捶揲工艺“是利用金、银质地比较柔软、延展性强的特点,将自然或冶炼出的金银锭类的材料捶打呈各种形状,供进一步加工使用。捶揲技术可以追求优美而显现的艺术表现,既可以制作器物的形体,也可以制作装饰花纹”。

如都兰墓葬出土的镀金银质鹿形饰片、镀金银质鐏饰片及立凤银饰条、银饰片中的立凤身部和缘饰,经捶揲技法加工后,纹样平整细腻。而阴线雕刻的手法使的金银器刻画的动物、人物形象更加生动。
鱼子纹和联珠纹
与出土棺板画和丝织品一样,粟特系统金银器中也有大量的联珠纹饰,联珠纹饰的含义在上一节中已有较为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在都兰方形立凤环状忍冬纹银饰片中的立凤翼部可见联珠纹样。

鱼子纹,顾名思义,在金属饰片(条)中以许多小圆点组成的辅助纹样饰地。这种鱼子纹在都兰夏日哈一号墓中出土的镀金银质鐏片中可以见到。
忍冬纹
忍冬纹的运用极其繁杂,几乎青海都兰墓葬出土的每件金银器上都有忍冬纹饰。同时期的唐代器物上也运用忍冬纹进行装饰,但将二者相比,就会发现有诸多方面的差异。
如,青海都兰的金银器忍冬纹一般为环状桃形,“采用三瓣花两片双钩状叶的形式”。而同时期唐代金银器中的忍冬纹饰除了三瓣花的样式,还有五瓣花的样式。花中常有鸟、兽及人物的图案,形式多样;青海都兰金银器中的忍冬纹饰排列方式上多为纵列式、横列式和四方连续式,花与花之间连贯性较强。
同时期唐代金银器中“花结多置于桃形或莲形的分割区域内,彼此不相连贯”。且都兰出土的立凤图形中,多处饰以忍冬纹,尤其立凤嘴中衔着忍冬纹和颈后饰有忍冬纹,这样的图形在同时期唐代立凤形象中未曾见到。
这些都说明都兰出土的金银器应不是中国生产,许新国先生认为“都兰金银器在题材和造型上与中亚粟特人所使用的金银器纹样非常相似”
结合韩伟编著的《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一书、日本学者桑山正进的《一九五六年以来出土的唐代金银器及其编年》一文等材料,许新国先生将这批“都兰金银器的年代定在武则天到玄宗时期,墓葬的年代定在盛唐时期”。
文物的定期及墓葬年代的确定,为我们进一步研究青海都兰出土金银器提供了线索,可以将其与同时期唐代的金银器进行比对。
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所藏“有翼骆驼纹瓶、带把手杯、忍冬纹带把手杯、鹿纹三足盘、方口把手动物纹容器、野生山羊纹单耳杯、野生山羊纹盘、男女神饰片、两件佛像饰片”等十件金属器物,这是目前已掌握明确为粟特系统的金银器。
从这些器物来看,粟特金银器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金银器大多以整片金属制成,一般在质地柔软的模具上进行铸造和捶揲,使整片金属形成各式造型;第二,金属制品多运用捶揲及阴线浅刻的技法。
第三,主题纹样之外,辅助纹样一般以鱼子纹填满空白,器物上也多见联珠纹饰;第四,“无论主饰和辅饰,均大量使用一种独具特点的忍冬植物纹饰。这种忍冬纹饰多采用三瓣花形两片勾叶的形式”。
这几个粟特金银器特点恰好与我们上述分析的青海都兰出土金银器的铸造工艺和图案纹饰几乎吻合,通过比对可知,“都兰出土的这类金银器同中亚粟特人所使用的金属器纹样上非常近似,总体风格是一致的”。器物年代多在七世纪后半叶到八世纪前半叶。
以上所述为都兰出土金银器的铸造工艺和图案纹饰,其中蕴含了诸多粟特文化因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的唐代金银器也蕴含有粟特、波斯等西域文化因素。这就涉及到中亚粟特金银器对唐代金银器铸造的影响。
19世纪末俄国学者马尔沙克在《粟特银器》这本书中他揭露出粟特银器的面貌,认为“粟特银器可分成带萨珊风格,本地特征和接近中国银器这三个流派”。且马尔沙克认为“从7世纪到9世纪早期,粟特与中国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中国的金属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亚器皿的影响;反之亦然,粟特器皿装饰上也会出现唐风”。
999年,齐东方教授的《唐代金银器》一书无论从资料、视野、论述,这都是一本研究唐代金银器的集大成著作,书中关于粟特金银器与唐代金银器之间关系的部分内容也有其拜访请教马尔萨克教授所得。
“唐代著籍粟特人中,一部分从事于手工业,粟特人精于波斯风和中亚风的银器、铜器的制作,也精于制革”。
日本学者桑山正进也认为“中亚地区,特别是粟特地区的银器,给予了唐代的深刻影响”。而唐代时期的部分金银器,正是雄踞于青藏高原的吐蕃人进献给唐朝的,所以我们在讨论粟特金银器与唐代金银器中间的关系时,也要注意吐蕃在这之间发挥的媒介。
霍巍教授在其《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一书中对此有过较多论述。此外,粟特系统特有的金银器品种(如胡瓶等)在青海都兰一带墓葬中尚未发现,但在棺板画中有所体现。而新疆、内蒙古、陕西、山西等地都有出土粟特系统特有的金银器品种。
吐蕃与粟特的关系
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同为游牧民族的粟特和吐蕃人之间有着诸多往来,可见粟特人虽臣服于西突厥的统治之下,但是西突厥对吐蕃的控制较为松散,并且西突厥依靠粟特人强大的经商能力进入欧亚大陆从事贸易获利。同时,粟特人在西突厥部落中传播祆教信仰,主持祆教仪式而获得较高地位。
后来,在吐蕃一步一步控制了西域广大地区后,吐蕃人与位于中亚地区的粟特人有了更多地直接接触。两个民族在河南道的交通路网下实现了多方面、全方位的交流,比如生活习俗、日常用品,甚至粟特人的祆教信仰也在吐蕃地区流传。
“在两《唐书》、《册府元龟》、《唐会要》等文献中,记载吐蕃历年向唐朝贡、赠送之物中,尚有金鹅、金城、金瓮、金叵罗、今胡瓶、金盘、金碗、玛瑙杯及银制犀、牛、羊、鹿等各种金银器,其中有些当系来自粟特或受粟特影响制作”。
此外,河南道青海地区出土的棺板画中所绘人物服饰也与粟特人的服饰有很大的相似性,应为粟特人与吐蕃人或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人交往过程中,吐蕃借鉴后融合了自己民族特色的元素进去,适宜在高原和特定场合下穿着。
总之,借助丝绸之路河南道及其他路线,吐蕃(包括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人)和粟特两个民族,因为地缘和各自民族的特点,“不仅沟通着东西方之间物质文化的交流,同时也沟通了东西方精神文明文化的交流”。
粟特民族流动性和适应性极强,将带有中亚、西亚,甚至欧洲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带到了中国,而吐蕃民族既有北方草原的文化特点,又有中原传统的汉文化特点,这些特点必将造成两个民族之间的思想交流与文化激荡,推动了南北朝隋唐时期民族大融合与丝路文化交流互动新局面的形成。
结语
总的来说,粟特人在南北朝隋唐时期不断向东迁徙,依靠丝绸之路与沿线不同民族、国家进行商贸往来的情况下,与青藏高原临近的蜀地也进行过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